他的个人生命史 也是台湾战后历程的时代史
文/陈雪梨
书名:《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放胆两岸波涛路》
作者:曾健民
出版社:联经出版
出版日期:2015年11月11日
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文惠姐提到,家父每天晚餐时要和家母聊天,将一日之事和她叙说一番。作为家中的老么,小时候跟着爸妈来来去去,在父亲的朋友圈里,被取了个「秤锤」的绰号,好像总是挂在爸妈的手臂上。也因此,从很小的时候,就听了许多似懂非懂的情事。父母聊天的时候,时不时就要提醒:家中听说的事,外面千万不能去说,如有陌生人搭讪,不要说什么,可能是特务向小孩子探听消息!「特务」这个名词,记忆中好像比什么叫「电影」还要早知道。确实,当时我们住在北投的泉源路上,是蒋介石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家中不定期就有陌生人闯进来「查户口」,一种莫名的紧张气氛,像罩顶的乌霾一样,在小小心灵中留下了印象。不知始至何时,就知道有二二八这样的事。家父每次隐晦的谈起,就有一种肃杀沉重的语气。他会谈起某某某,二二八失蹤了,某某某,他被枪杀了。他说台北律师公会二二八前有多少人,二二八后剩不到一半。到上小学时,才知道有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共产党是万恶的这些话,但没有多久,就已习惯性地把校长朝会的训话,国歌里的「吾党所忠」当做是耳边风的反面教材,学校里、同学们的世界和家里、大人们的世界,有着不同的肌理和色彩。
另一件和别人家不同的地方是,家父喜欢把「男女平等」挂在嘴边。可能因为是寡母带大,家中四个女儿,他又和妈妈特别谈得来,他确实由心底认为男女应该平等。文惠大姊考大学时原来是想读理科,他天天希望她读法律,继承他的志业,终于如愿以偿!回想起来,我的潜意识中还真没有所谓「第二性」(second sex)的影子,从小不喜欢玩洋娃娃,也从来也不会以为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就觉得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美国甘乃迪总统遇刺身亡,副总统詹森无缝对接继任总统。爸爸每天盯着报纸,听收音机,在餐桌上对妈妈和十一岁的我述说着美国民主宪政的稳定是多么难得。
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国戴高乐总统宣布中法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爸爸又是每天盯着报纸,听收音机。有一天,他面色沉重,在餐桌上宣布他决定要竞选台北市长,他说一个变化的时代又将来临,他希望台湾人能多一些行政人材,不要一碰到变局,就很无助地束手无策。他说高玉树告诉他这次不准备参选,那只好自己来了。(当时他没想到高后来还是宣布参选,那时他已无法退选。)
选举时,我小学五年级,休了几个月的课,跟着大人当「秤锤」。爸妈对我没去上课,好像也不在意,大概是相信我不会留级。对于那次选举,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演讲时用沙哑的嗓门,声嘶力竭地讲述着没太多人在意的党外政见:废除戒严法、民主宪政、都市计划…。
家中,尤其从北投搬到台北后,始终有许多人来来往往。每天下课回来,总不知晚餐桌上会有多少人共餐,每天听着各式各样的言论。家中有一个当时算罕见的冰箱,里面随时都有吃寿喜烧的冻肉、洗好的大白菜。每来一位客人,妈妈就添一付碗筷,发一个鸡蛋,调料自己来,冻肉、白菜不够了再拿一盘出来。客人中除了爸爸的酒友、棋友、「文化仙仔」,姐姐的同学、朋友,还有日本客人,美国客人。大家高谈阔论,什么都谈,那时的监听技术大概还没有太发达。
犹记有一次,爸爸与美国使馆一位常来的朋友谈论台湾的前途。爸爸提到波兹坦宣言、开罗宣言、联合国、人权、民主宪政等等,对着以国际力量来对应国民党政府的苛政抱着期待。柯先生操着熟练的国台语,说:「陈先生,您要知道,美国人不会为台湾人出什么力的,美国人是现实主义的,台湾人只有靠自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现实主义」这个名词。
从小,爸爸要我们不要迷信、不要怕黑怕鬼。他不让人向我们(至少是我)讲鬼故事。北投家中周遭是一圈院子,到晚上除了月光,几近伸手不见五指。他和妈妈坐着聊天,小孩子们只要绕屋子走一圈,就给一角。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是我的第一桶金!
他常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大学时和同学打赌,到乱葬岗去过夜。他说他喝了点酒,就去了。当时也不能说没有点毛毛的。但他壮下胆,演说起来:「请各位知道,我是东大学法律的,各位朋友如有什么冤屈,可以来告诉我,我会尽力替你们伸冤!」结果,一夜无事,他就此认为没有鬼神这类的事。
爸爸确实也有着丘罔舍的爱玩闹、幽默、有点创造力的一面。他喜欢钓鱼、看鱼。由北投搬到台北后,住在楼房里,没有养鱼的条件。他就异想天开,将楼顶的天台涂了层防水漆,放了浅浅的水,养起耐命的泥鳅起来!当时我还在初中,住在顶楼,霸佔着家中唯一的唱机,一面听华格纳的歌剧,一面听由屋顶漏到接水的几个脸盆里叮咚叮咚一下的声音。这个实验大概持续了不到半年。
高中时,日本友人介绍了一位日本「救世教」的教主和他的几位教友来找爸爸。救世教认为可以用心力帮人治百病,基本上,就是集中精神,对着病人举着手掌相向,病人就有所感!他们在家里做了几次示範性的治病聚会,好像对某些人还真有点效果。每日家中,各式各样的病人居然就多了起来。接着,日本教主就让爸妈也参加治病的行列。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煞有介事,举着手掌,像个观音娘娘,在帮人治病。从小的理性主义训练,让我忍不住躲到房间里噗滋噗滋地笑。问爸爸到底在干什么,他很严肃地说:「这样特务才不会怀疑我们家为什么一天到晚有那么多人出入!」哦,原来如此!结果,有一天回家,居然看到我们一女中的教务主任也在病人行列。从此,我多了一个black mail的对象。在学校里迟到早退、逃课,就更有恃无恐了!
一九七一年,几位日本年青人来访,送了一盒羊羔,没多久,特务就到家里来把父亲和羊羔带走了。那时我大一,住在台大对面新生南路的一条小巷子里,家里的禁书、自己从牯岭街搜来的各种书刊都跟着我搬出来,堆在小房间的床下,地上,也是万幸,这些东西当时不在家里。妈妈特地叫人捎信给我:爸爸被抓了,你暂时不要回家,也别打电话。那时两个姊姊都已出国了,我的户口好像还挂在北投,故特务们一时还搞不清家中还有我这个女儿。犹记那时在黑夜里的台大校园,我芒茫然一个人走着,不久前,朋友们还为了保钓在这里挂长布条标语,我的一位法国朋友还带着那时罕有的一部专业级照相机在校园里到处拍照。大家激情万丈,但我还能自由多久?会不会牵连到大家?如果被酷刑,我能挺住吗?走到校园尽头一个偏僻的公用电话亭,我打了个电话给柯先生,「爸爸被带走了」,后来知道他马上将消息传了出去,纽约时报上登了陈逸松被捕的消息。打完电话,已是将近深夜,我搭了最后一班公车回家,在家对面隔着宽阔的松江路看附近好像暂时没人盯梢,我就已最快的动作过了街开了门锁溜进家里。妈妈还没睡,我和她说已给柯先生打了电话,她说她已到处奔走,在探听爸爸到底被哪个特务机关带走,带到哪里。天未亮,我又由家中溜出去。
那盒羊羔,幸好爸爸先放在祖母灵前,没有打开过。警总的人拿走看了也知道确实是羊羔,不是炸弹,家里有个坏掉的闹钟,爸爸手痒拆过,没装回去,特务们原以为是製作定时炸弹的道具,后来大概经专家鑒定过确认不是。也可能是纽约时报的小段新闻发挥了一点制约作用,没多久,爸爸终于回家了。我们见到他,彷如隔世!
如今他下半生的回忆录终于即将出版,有幸得以藉此缅怀他日常家居的二,三事以识怀念之情。
●本文摘自联经出版《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放胆两岸波涛路》
关于《陈逸松回忆录》
陈逸松是日本殖民时期的第二代台湾人,这一代人并未见证由清入日的改朝换代大震动,而是在殖民统治进入稳定期后才出生,接受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教养。而这一代台湾知识分子求学、成长时恰好遇上全球性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期,受到世界思潮之影响,一方面痛恨殖民地歧视统治,一方面怀抱左翼理想,而且在他们最有活力的青年时期迎来了日本殖民终结、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时代巨变。
这群「新台湾人」从1930年代开始活跃于政治、文化、经济的舞台,此后至1950年代为止的大变局中,有人入狱,有人冤死,有人逃亡,或者沉默噤声。陈逸松身为其中的一分子,他的一生经历足以见证台湾从殖民到战后的历程,本书所述即为其战后时期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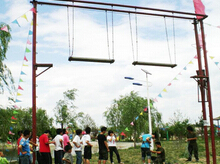




 melbourne,
australia
melbourne,
australia 4000-288-501
4000-288-501 010-57019853
010-57019853 weiyouwei6@yeah.net
weiyouwei6@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