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惩劝-浅谈杜维运与其治史态度
史学家杜维运生于山东嘉祥的一个农村,累代以务农为业,父亲早逝,由母亲经营垦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四处流窜,家乡沦为中共之手。杜维运踏上流亡之路,母亲遭到共产党杀害。1950年渡海来台湾,靠政府奖学金完成大学学业,后执教于大学。1964年与孙雅明女士结为连理,落居于台北市区。
杜氏于1950年冬对史学发生兴趣,台大历史硕士论文即以清乾嘉史学为研究对象,他自谦沉醉于清代几位大儒的史学之中。1962年秋天,杜氏负笈英国剑桥大学,将目光自中国移向西方,充实西方史学史及史学理论、方法。归国后,致力于融合中西史学方法,以澄清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的误解。1987年开始进行中国史学史编撰工作,1993年完成先秦两汉史学。
教学之余,杜氏致力于史学史撰写工作,先后完成许多着作,荣获教育部学术奖等奖项无数,杜维运生平着述并载入世界学人传。杜氏着作等身,主要有《史学方法论》、《与西方史学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清代史学与史家》、《赵翼传》、《忧患与史学》、《中国史学史》等。
杜维运的治史态度可从杜维运的作品中看出,如同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言,是「惩罚暴君的鞭子」,虽然他打在古罗马皇帝身上,却痛在一切专制暴君的心上。杜氏倡言「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典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他认为,写史必须除了写真的历史外,进一步冶善与美的历史,是史学上的盛事。
西方史学家塔西陀在《编年史》指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然而杜维运认为史学的危机在于对邪恶人所起的吓阻作用失效了,尤其他认为现代史学已经失去维持人类文明的功能,因此杜氏认为挽救史学的危机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撰写开始着手进行。杜氏研究史学史特别昂扬「君举必记」的观念,如同塔西陀所言「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
历史记载「人类的功业」,却也记载了「人类罪恶、愚昧与不幸的记录」,杜氏认为这样的「记录」是出自于史学家有意无意的製造。史学家如果不写人类良善的历史,杜氏认为问题不在于历史的本身,而在于史家的见识。他认为史学家的胸怀与见识是史学上最关紧要之处,他也认为史学家要衡量历史事实的真伪虚实,并斟酌历史对当代与后世所发生的影响,而精选真善美的素材以写成人类福音的历史,那么历史便能彰显「人类的功业」,因此史学家对史学史的撰写,便成了刻不容缓的工作。
有宏观的历史视野,是杜维运多年来治史的态度,也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史学家。清代学者方孝孺说:「史氏者所以掌罚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于世」。杜维运认为历史在于「以史惩劝,以史制君」,如同「惩罚暴君的鞭子」,痛快的打在专制暴君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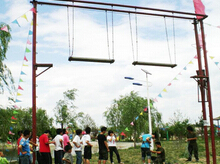




 melbourne,
australia
melbourne,
australia 4000-288-501
4000-288-501 010-57019853
010-57019853 weiyouwei6@yeah.net
weiyouwei6@yeah.net